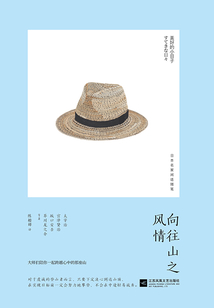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導讀:深植于靈魂的愛山之心
廖秀娟
本書收錄了十四位作家的十七篇作品,十四位作家中,七位是日本近代知名的文學家,七位是職業登山家。以日本第一高山富士山為題描寫的作品有小島烏水《雪中富士登山記》、太宰治《富岳百景》《關于富士》、若山牧水《駿河灣一帶的風光》、坂口安吾《日本的山與文學》,以及作家近松秋江以富士山附近的箱根駒岳為題材的作品《箱根的山》;以日本阿爾卑斯山脈槍岳、穗高岳為主題的作品有芥川龍之介《登槍岳記》、早川鲇子《于穗高岳屏風巖》、大島亮吉《涸澤巖小屋的某一夜》;以巖手縣奧羽山脈為題的作品有宮澤賢治《那米床山的熊》;另外以高山四季風景、地形、溫泉、動植物為題的作品有高村光太郎《山之春》《山之雪》,以及木暮理太郎《山的魅力》、若山牧水《圍繞火山的溫泉》;描寫登山愛山之情的作品有職業登山家松濤明《懷山之心》、辻村伊助《登山早晨》、石川欣一《可愛的山》等作品。
依照日本山岳協會于二〇〇七年出版的《日本山岳會百年史》一書中的記載,日本人自古以來即習慣接近山岳,其中大部分是源自于山岳信仰所帶起的宗教登山或狩獵目的的登山。到了明治初期才開始有了以測量為目的的登山和為了調查地質、研究高山植物等目的的學術登山,而純粹以享受登山樂趣的近代登山在當時仍不多見。一直到了一八九四年志賀重昂的著作《日本風景論》刊登之后,才開始刮起日本近代登山的風潮。
山岳信仰是屬于自然崇拜的一種,特別是像狩獵民族等與山岳關系密切的民族會對險峻的自然環境抱持著敬畏之心,他們深信山岳之地是具有靈力的,越是人難以靠近的嚴峻山脈,產生的敬仰之情則越發深遠,這股畏懼大自然的力量之后則發展成宗教形態的登山。例如古代的日本神道信仰中,人民從森林中的水源、礦山、依附森林而生的動植物中取得了生存所需的供給,對此充滿感激的同時,雄偉的山勢、轟隆振動的火山噴發也引發當時日本人對山岳以及森林的懼怕敬畏之心,因此他們在各個大山中建立神社,祈求山之御神可以降臨坐鎮,這當中最為人所知曉的就是富士山。
眾所周知,日本國土山岳面積約占百分之七十三,因山高地險、火山頻起,使得日本山岳信仰特別深厚顯著,成為信仰崇拜的高山有三百五十多座。富士山標高三千七百七十六米,是日本第一高的活火山,自古以來富士山即被視為神體山,富士山信仰最早可回溯到公元八世紀,《常陸國風土記》中曾經描寫被冰雪所籠罩的富士山峰景色絕美卻又孤高難以親近,結合了人們對其的崇敬與畏懼。山頂上的萬年雪匯集成了豐富的涌泉,提供給山麓居民農耕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源,同時反復的火山噴發所造成的自然災害也使其成為人們恐懼畏怯的對象。從八世紀末到十一世紀末依《續日本紀》《日本紀略》兩書的記載,至少歷經九次火山噴發,日本人為了企盼火山之神不再噴發,便于火山噴發口附近設立神社祭拜淺間大社,祈求天下太平與富士山的靜謐。自此,富士山成了人們遙拜和崇敬的圣山,成就了日本的靈山信仰。到了十二世紀,由于富士山的火山活動進入平穩期,固有的富士山崇拜形式也從遙拜轉化為登頂朝拜,更是宗教修行的修驗場,修行者圍繞著富士山域進行登頂參拜以求得驗力。直至近世,富士登山多以信仰登山為主,但是至明治維新后出現變革,逐漸轉化成觀光與近代登山形態的登山。
日本近代文學家中有多篇作品是以富士山為背景撰寫的,例如夏目漱石的《虞美人草》《三四郎》;泉鏡花《婦系圖》;北原白秋《云母集》《觀相之秋》;齋藤茂吉《赤光》;若山牧水《山櫻之歌》《駿河灣一帶的風光》;太宰治《富岳百景》;武田泰淳《富士》;武田百合子《富士日記》等作品。當中最為人知的即是本書收錄的太宰治作品《富岳百景》,豎立在御坂卡(山梨縣富士河口湖町)上的太宰治文學碑上,刻印的就是本作品末尾“燈籠草與富士山很搭”一詞,這是人人皆能朗朗上口的名句了。太宰治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是青森貴族院與眾議院議員津島源右衛門的六男,二十歲時曾經因為思想性困擾企圖自殺,獲救后隔年進入東大法國文學科就讀,在此時遇到了他文學創作上的恩師井伏鱒二。《富岳百景》撰寫之時,正是他與小山初代相約自殺失敗之后分手,因藥物中毒開始過著頹廢生活的時期。一九三八年初秋,他抱著重生的決心與覺悟,前往山梨縣御坂卡山上的天下茶屋,這是井伏鱒二閉室撰寫文稿的地方,九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間,太宰治朝夕與窗戶外的富士山相望,并且在井伏的介紹下與之后的夫人石原美知子相親,于隔年一月完婚。透過作品《富岳百景》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他在這三個月日日望著富士山,透過山的雄偉與大自然的單純而取得了心靈上的平靜,開啟了他生命中精神狀態最為平穩的中期時期,再將他的創作推上高峰。
作家若山牧水以漂泊與愛酒而聞名。一八八五年八月出生于宮崎縣尾崎山的北麓的醫生世家。他的一生可說是在旅涯中度過,他曾說“我的詩歌是我每個時期生命歷程的碎片”,經常寫詩歌詠富士山的他于一九二三年出版的歌集《山櫻之歌》中,有多首歌詠富士與櫻花的詩歌,更將次男之名取名為富士人,由此可見他對富士山的喜愛之情。《駿河灣一帶的風光》中描寫的是從駿河灣遠眺雄渾壯美的富士山景,文中有多首若山牧水歌詠富士山的詩歌。
近代登山(alpinism)一詞出現于十九世紀后,如語源所示,阿爾卑斯山脈成為運動性質的登山對象,比起一般的爬山健行,近代登山所意指的是具有攀爬如阿爾卑斯山脈難度的高超登山技術與專門裝備,伴隨著山高險峻難以攀登等條件。日本的近代登山起始于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由當時明治政府從英國聘任到大阪造幣寮(現造幣局)擔任外國技師的威廉·高蘭德等人所傳入的。他于一八七二年來到日本,一八七四年首次使用近代登山專用的冰杖和登山釘鞋攀登六甲山,之后于一八八一年攀登槍岳和前穗高岳,并將此地命名為“日本阿爾卑斯”,之后日本山岳會初代會長,亦是本書作家之一的小島烏水將之再細分,命名為“北·中央·南阿爾卑斯”。
小島烏水是位擁有多重面向的登山者,他不僅是位銀行家,亦是山岳登山家,紀行作家,文藝雜志編輯,冰河地形研究家,浮世繪的研究者。一八九四年受到志賀重昂《日本風景論》一書的啟發開始了山岳登山,一九〇二年與友人岡野金次郎成功攀登槍岳之后聲名大噪,一九〇三年與多次前來日本攀登高山的英國傳教士瓦特·威士通見面,瓦特·威士通曾寫下《日本阿爾卑斯的登山與探險》一書,將日本阿爾卑斯山系的美麗推展到世界,被尊稱為日本登山之父。小島烏水接受他的建議,仿效英國山岳會成立了日本山岳會。從此日本近代登山熱潮席卷,正式進入日本阿爾卑斯探險的黃金時代。不只專業的登山領域書籍,小島烏水的姓名也曾多次出現在日本文學的作品中,例如芥川龍之介《槍岳紀行》一作中曾經提及小島烏水攀登槍岳一事,太宰治《富岳百景》也曾言及小島烏水之名,由此即可知曉他對于日本近代登山的貢獻與重要性。
穗高岳、槍岳位于日本中部山岳國立公園中的飛驒山脈,又被稱為日本北阿爾卑斯,是登山愛好者的憧憬路線之一,因此也經常成為登山作家紀行文的題材。穗高岳標高三千一百九十米,由奧穗高岳、涸澤岳、北穗高岳、西穗高岳及明神岳合稱為穗高連峰,是日本的第三高峰。穗高岳與劍岳、谷川岳合稱為日本的三大巖場,本書中收錄的作品《于穗高岳屏風巖》中,所描寫的地點即是位于穗高岳的屏風巖,此地被喻為日本國內最頂級的巖場,登山客攀巖的至難之地。早川鲇子是作者的筆名,本名為佐宗ルミエ,與之后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女性登山者田部井淳子是共同登山伙伴,早川在一次冬季攀爬谷川岳巖場時為拯救隊友不幸墜山死亡。繩索、巖釘、腳底下百尺的黑暗深淵,作品中透過作者的視點,讓人一窺登山者高山攀巖時與死亡相伴的驚戰。
槍岳是日本第五高峰,標高三千一百八十米,位于飛驒山脈南部,因為受冰雪侵蝕山形如朝天之槍,相當尖銳陡峭,亦被譽為“日本的馬特洪峰”,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高山之一。穗高岳、槍岳等高山因地勢險峻有多位登山者遇難葬身于此,例如本書收錄其作品的作家松濤明、大島亮吉。松濤明被喻為天才登山家,十歲開始爬山,年僅十四歲就完成一年二十次的登山,十五歲完成日本冬季北阿爾卑斯山攀登,十六歲進入山岳會后陸續刷新多項高山攀登紀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嚴冬季節縱走槍穂連峰之時,隊友有元克己摔落山谷已無氣力再攀爬上來,他不忍隊友在風雪中孤單死亡,決定下至山谷共同赴死,他到臨死前撰寫的日記與遺書于隔年七月雪融之后與遺體同時被發現,享年二十六歲,之后出版社以《風雪中的緊急露營》之名將他遇難時的日志、遺書出版,被譽為日本山岳小說的經典,從本書收錄作品《懷山之心》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的愛山之心。
另一位登山作家大島亮吉是慶應義塾山岳會員,在大正后期及昭和初期,日本登山界開始追求所謂的“更高、更艱難”的登山形態時,他即以北阿爾卑斯雪板登山、槍穂高連峰積雪期登頂、攀巖、北海道探險登山等壯舉躋身當時登山界的風云人物,二十九歲于前穗高岳攀爬中墜落喪生,生前曾經翻譯和介紹了多篇西歐的山岳文獻帶動登山思潮,也撰寫多篇高山攀登的紀行文與隨筆,頗受登山者的愛讀,作品于過世后收錄至遺作《山——大島亮吉紀行集》,本書收錄作品《涸澤巖小屋的某一夜》即是他重要的一篇遺作隨筆,在作品中他曾寫下自身對于山岳與死亡的思索,是了解他對山岳情感與面對死亡的重要作品。
芥川龍之介是言及槍岳一定會被提起的日本近代文學作家。一般人透過他譏諷口吻的作品風格與照片中略帶神經質般的表情,很難想象他是一位在中學時期曾經加入體操社團、擅長游泳的運動健將,進入大學之后更將熱情傾注于登山、旅行當中。當時日本的年輕人受到前述英國傳教士瓦特·威士通所宣揚的——透過登山來體驗人生喜悅的西歐登山觀影響,紛紛傾心于山岳的浪漫情懷之中。年輕的芥川也不例外,他當時熟讀志賀重昂的《日本風景論》和小島烏水的作品《山水無盡藏》,總是向友人熱情地訴說槍岳的魅力與登山的樂趣。一九〇九年在學友的邀約下一同前往上高地攀登槍岳,回來之后他將這趟槍岳的登山經驗寫了三篇作品,分別是《登槍岳記》《槍岳紀行》以及自殺前五個月寫下的晚期代表作品《河童》。二〇〇八年為了紀念當年十七歲的芥川少年槍岳登頂一百周年,出版了《芥川龍之介的槍岳登山與河童橋》。他曾經說過在他心中,中學時期快樂的登山回憶總是光彩輝煌。與這充滿了苦痛的俗世不同,上高地成了只出現在他記憶中早已失去的理想鄉。
而以《銀河鐵路之夜》一作聞名的宮澤賢治是一位擅長山中健行且深愛大自然的作家。他中學時的學友曾提到宮澤賢治的運動神經遲鈍,棒球、柔道、劍道等運動都不拿手,時常惹軍人退役的體育老師大發脾氣,但是不可思議的是他竟是位登山健行高手。他從小學時即爬遍周遭的山丘森林,就讀盛岡高等農林學校時為了進行土性地質調查,足跡踏遍巖手縣各地,縣內的巖手山、早池峰等都是他經常攀登的山群,也曾溯溪而下或是在松樹林下野宿,熱愛巖石喜愛收集礦物、熱衷觀星。從他的童話與詩歌等作品都可以看到許多有關高山、森林與自然風景的描寫,并勸勉人類要存著敬誠的心來珍惜大自然。
除了以上這些以日本高山為題的作品之外,本書也收錄了多篇描寫高山植物、地形與四季風景的作品,許多是選自職業登山家的登山紀行文,例如木暮理太郎《山的魅力》、辻村伊助《登山早晨》、石川欣一《可愛的山》等,撰寫的風格不同于文學家,在他們的筆下字字滲出對山的仰慕之情,攀上頂峰后,寂靜孤高的山尖上因氣候關系盛開的一朵朵靈巧的小花隨風搖曳,眼前除了峻偉的山景與動植物之外再無其他,它們的陪伴讓每一位登山家在寧靜中更加愛山,至死不渝。
本書借由七位登山家與七位文學家的作品,以遠近交錯的視點,透過閱讀或是與他們同時單靠著腳下巖釘,在嚴冬冰雪肆意的吹襲下孤零零地懸空高掛在萬丈的絕壁上,或是帶著對生命無助的絕望與渺茫的希望來到富士山的懷中祈求重生,讓我們穿上釘鞋,帶上冰杖、巖釘,逐一推敲他們文字中深植于靈魂的愛山之心。
作者廖秀娟,日本大阪大學文學博士,元智大學應用外語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