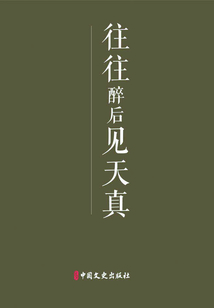最新章節
書友吧第1章 傅抱石先生的生平和作品
第一輯 藝術人生:待細把江山圖畫
黃苗子[1]
一、金剛坡下
記得1943年的一個秋夜,我從重慶城里坐郊區公共汽車到70里外金剛坡下賴家橋,那個地方背靠金剛坡,崇山茂林,廬舍成列,好一片典型的巴蜀山村風景。那里是當時的政治部第三廳一部分宿舍所在,住著幾家文藝工作者,其中有畫家傅抱石和李可染等。
第一次認識傅抱石,是在重慶文藝界的一次集會上,是經過徐悲鴻先生介紹的,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坦率、樸素、對朋友一見如故。我這次到賴家橋還是他寫信約我去過周末的。傅抱石當時雖然已是略有名望的畫家,但是處在那個時代,藝術不值分文,更兼他的子女多,收入少,在物價一日數漲的“陪都”社會里,抱石一家經常有斷炊之虞,可是畫畫寫作,始終是他的第一生命。他愛朋友,愛酒,愛他自己的美術事業,家務事大都由傅夫人羅時慧女士張羅,只是依靠這位賢內助的安排,生活重擔對他的創作還不致成為嚴重的威脅。
在賴家橋傅家,除了欣賞他的大量作品和海闊天空地談論藝術,談論時事之外,我偶然問起他是怎樣開始畫畫的,他對我說:做孩子的時候住在南昌,隔壁恰好是一家裱畫作坊,由于老跑去玩,就認得那里的一位專門修補古畫的卓(或左)師父,老師傅對天真聰明的傅抱石十分喜愛,就給他講解和觀看很多古今字畫,從此他便對繪畫感興趣,開始鉆研繪畫的。那天晚上,由于喝了幾盅,抱石的興致更高,就滔滔不絕地同我談到他的半生經歷,由于這位藝術家很不平凡的身世,使我感到極大興趣,因此30多年前的這一夕話,至今還是縈回在我的腦子里。
二、從巖石縫中掙扎出來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8月,江西省城里一家以補破傘為生的窮苦人家,生下了一個孩子。這娃娃的祖籍是南昌西南的新喻縣(今稱“新余”)章塘村,父親是孤兒,是個從小當長工(雇農)喝苦水長大的窮苦人,受盡了地主老財的打罵,得了肺病,不能扛重活。在農村里沒有飯吃,便流落到南昌城,學了一門補傘的手藝,每日挑著擔兒穿街走巷胡混兩餐。娃娃的母親是個逃跑出來的童養媳,這一對同病相憐的苦男女結為夫妻,生育過六個兒女,現在又生下這第七個男孩,但因生計實在艱難,孩子先后夭亡,這最小的一個娃娃也就成為僅存的一個了。
這個孩子就是后來的著名畫家傅抱石。
傅抱石才開始懂人事,父親就因生活的煎熬,加劇了肺病,在一個凄慘的夜里咽了氣。母親是個意志堅強的勞動婦女,為了養家糊口,便毅然挑起了丈夫生前的擔子,繼續干這補傘的營生,后來實在無法糊口,就把未滿10歲體弱多病的抱石送到一家瓷器店里當學徒。江西的瓷器是有名的,但制造瓷器的工人卻都是無名之輩,尤其是學徒,在舊社會里是被壓在最底層的。這個本來就孱弱的孩子由于操作過重,得了癆傷之癥,終于被老板趕回了家。母子對泣一場之后,母親也就只好兼做替人洗衣的工作,給孩子掙錢養病。
上面說過,傅家的隔壁是一家裱畫作坊,這家作坊規模很小,在西鄰;東鄰則是一家收買破爛兼刻圖章的刻字攤。稚氣十足的抱石常常到東邊去看人刻印,西邊去看人裱畫來滿足他那童年特有的好奇心。看得多了,他自己也就在家中刻刻畫畫,鄰里看見這孩子聰明好學,有的就主動集資幫助他進私塾。兩年后輟了學,又有一位小學教師看見他求學心切,就幫助他進了高等小學。因為畢業成績優異,被保送進入師范學校。傅抱石就這樣結束了他的童年。
在師范學校,傅抱石付不起書籍學雜費用,母親又染上了肺病,雖然校長給他半工半讀的機會,讓他管理學校的圖書設備,總算解決了上學問題,但家庭生活的愁苦,也使他不得安生。那時學校有一個叫老張的看門工友,認得城里幾家士紳人家,他們都愛收藏古印,老張看見傅抱石的圖章刻得好,便建議他刻幾方摹仿趙之謙的印章試著拿去賣,總算傅抱石的技巧不壞,冒牌的趙之謙居然賣得了價錢,母親的生活醫藥得到維持了。可是日子長了事情就拆穿,買圖章的人跑到校長那里去告發。偏巧校長是個愛才的人,他對傅抱石說:“既然能亂真,以后就用自己的名義去刻印,不是很好嗎?”抱石受到鼓勵,從此就開始為人治印,因為求印的人多,收入也有了,就能夠買些顏料宣紙,開始練習圖畫,傅抱石每天上學,都經過一家舊書店,他經常抽空到那家鋪子去看有關美術的圖畫,往往鋪子關門都舍不得走。日子久了,老板被這個青年人的勤奮好學所感動,就答應借書給他看,每天限借一本,傅抱石大喜過望,從此就廢寢忘餐地苦讀,抄下了許多畫史畫刊的資料。據他自己說,他在那個時候,曾花了7個月時間,寫了十幾萬字的《國畫源流述概》稿本,那時他還未滿20歲。從這一點看,傅抱石早年就是非常刻苦鉆研的。
24歲那年,傅抱石在師范學校畢業,因為成績優異,留在學校附小當教師,不久改在江西省立第一中學擔任高中藝術科的教師。可是當時有一些大學專科出身的同行嫉妒傅抱石,認為他不夠資歷充當中學教職,傅抱石被控告到教育廳里,不久,他就離校失業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為找職業奔忙,當過臨時工,畫過廣告畫,又過著朝不保夕的困窮生活。但也正在這個時候出版了他第一部美術史的著作:《中國繪畫變遷史綱》。這時,由于他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受到了徐悲鴻先生的賞識,徐悲鴻看到這位年輕人的才能,了解到他的境況,終于通過這位肝膽照人的畫壇前輩的揄揚,傅抱石接受了為江西景德鎮改良陶瓷的任務,得以于1933年到日本去留學。
傅抱石在日本帝國美術學院專攻雕塑及東方美術史,并繼續鉆研繪畫篆刻。那時他認識了美術史家金原省吾,并把他關于中國美術的著作向我國讀者介紹,另外他對日本畫家橫山大觀、竹內棲鳳、小杉放庵等的作品,也深入研究,從中吸取養素來豐富自己的技法。這個時期,郭沫若先生正在流亡日本,傅抱石經常去拜訪他。郭老比抱石大11歲,他們的交情在師友之間,抱石經常把自己的理想和計劃向郭老請教。他在1935年完成的《中國美術年表》自序中,提到“與郭石沱先生道鄙意,亦重荷獎勖”的話。這位“郭石沱”也就是郭沫若。
傅抱石在日本,也以刻印賣畫補助學費,1935年他在東京舉行的個人作品展覽會,深得好評,金原省吾曾經稱譽他說:“君豐于藝術才能,繪畫、雕刻、篆刻俱秀,尤以篆刻為君之特技。君之至藝將使君之學識愈深,而君之篤學,又將使君之藝術愈高也。”[2]抱石當時就已經受到日本學者如此推崇,這并不是溢美之詞。
傅抱石是1936年離開日本回國的,這個因“資歷不夠”,而被迫離開中學教席的人,那時又由于徐悲鴻先生的介紹,在南京擔任一所大學的美術系教授。抗戰開始,抱石同所有具有民族氣節的藝術家一樣,到重慶參加了政治部三廳的工作,以畫筆從事抗日宣傳,但抗戰中期,三廳被解散了,家累很重的傅抱石,又一度過著賣畫刻印以酒澆愁聊以度日的困苦生涯,當時南京那家大學已遷到重慶,抱石只好又回去教書。
三、“待細把江山圖畫”
1950年以后,傅抱石開始了藝術生活的嶄新時期。
社會有一定的安定,藝術創作就繁榮起來,像傅抱石這樣有成就的藝術家自然受到尊重。當初他除了在南京師范學院教課外,還是江蘇省美術家協會的主席。后來他又當了江蘇國畫院院長,全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等。這榮譽,不僅在他少年時代靠“趙之謙”活命時夢想不到,就是在重慶托親靠友賣畫度日時也是夢想不到的。我于1964年春,曾在南京他家做客,那時他住在漢口路一座小山的別墅式樓房內,花木蔥郁,幽禽鳴春。有人說這就是乾隆年間有名的小倉山房舊址。他很有風趣地說:袁子才當年享受不到現代建筑的舒適,這一點他比不上我。再說,子才這座隨園,當年是靠當縣太爺巧取豪奪得來的,像我這樣一個寒士,要是生在他那個時代,不但無福住這座小倉山,恐怕還只能同鄭廣文那樣“焉知餓死填溝壑”呢!
1957年,傅抱石曾到東歐去旅行訪問,回來后出版了幾本寫生畫集,用國畫寫歐洲風光,這在過去是罕見的。1960年9月,美術家協會江蘇分會組織了以傅抱石為首的寫生團作了二萬三千里的旅行,他們經歷了六個省的十多個城市,后來在北京舉行了“山河新貌”展覽,為我國山水畫的繼承和創新,做出了新的貢獻。這個展覽,轟動了當時的國畫家們,對國畫山水的創作開辟了新路。1961年6月,他又作了一次東北寫生旅行,回來后出版了《傅抱石東北寫生畫集》。
1959年,這是傅抱石難忘的一年。那年8月他剛從外地寫生回南京,就接受了創作歷史上空前巨幅的國畫——《江山如此多嬌》的任務,這幅高5.5米,寬9米的大畫,是和廣東畫家關山月合作的。畫面上同時出現我國東西南北的不同地貌和春夏秋冬的不同氣候,有的部分正是萬紫千紅,春陽和煦,有的部分卻是白雪皚皚,山舞銀蛇,紅日普照,構成了“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的奇觀。傅、關兩位正是巧妙地運用我國傳統繪畫中把四季山水或四季花鳥集于一圖的妙諦,來表現廣闊河山的現實。
與此同時,國內外的大建筑或賓館、使館,都紛紛聘請他制作國畫。盡管他的身體從來就不算健康,但是他的藝術勞動卻是驚人的。這個時期是他的繪畫創作最旺盛的時候,而美術論著的問世,也是最多的時候。
40年來,傅抱石為了對藝術和對山河的熱愛,一直在忘我地工作,盡管他和古代許多畫家、詩人一樣愛酒貪杯,有時碰到二三知己,他也喜歡談天說地,但從不耽誤他的創作。他喜歡在晚上人靜時一個人作畫,有時直到通宵才睡,這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50年代后,傅抱石最愛用“待細把江山圖畫”這句詩句來題畫,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雙關語,10多年來,他辛勤作畫的心情,都表達在這句題識中。
抱石一直是以興奮的心情度過他的晚年的。按身體來說,他是抱著好幾種病在工作。酒對于他,在過去社會是借此澆愁,在他的晚年,則變成作畫的助力,但因此也剝蝕他的健康。1965年9月最后一天我們接到抱石在南京逝世的噩耗,他以61歲的年齡,結束了他的一生。如果拿齊白石來比,他只能算是中年夭折,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藝術界的一個損失呵!
四、石濤的道路
傅抱石早年在江西,看到了許多以清初四王為宗祖的山水畫,他就感到這種陳陳相因的風格束縛了山水畫的發展(盡管四王本身還是有成就的)。這時他發現了石濤,這個天才橫溢的大家,一掃當時的保守風格,以他自己從真山真水中得來的筆墨,寫出了大自然的宏偉恢奇,這使抱石十分佩服。到日本以后,由于當時日本藝術界人士如橋本關雪等對于石濤也十分傾倒,介紹過不少石濤的作品,這就加深了抱石對石濤的愛好。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余于石濤上人,可謂癖嗜甚深,無能自已”。[3]誠然,抱石是推重石濤的,他的作品例如畫面的結構方法等,有時也受石濤的影響,可是大家也看出,他的作品絕不是依樣葫蘆地模仿石濤的筆墨,而是從石濤的創作道路中,取得借鏡來表現自己對河山的思想感情。(石濤對于學習古人,反對學他的表面皮毛,而主張學他的創作用心,他說:“師古人之跡而不師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一頭地也,冤哉!”)因此他的畫可以說是從石濤出來但卻和石濤的面目又迥然不同的。
由于傅抱石從小就是自學,沒有拜過什么名師,他在學生時代正是五四運動以后,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同時他那時就已經從“裱畫作坊”里看到不少傳統的國畫,他在師范讀書的時候開始,一直到他的晚年,都不停地鉆研中國美術史,對于國畫的傳統源流,有比別人較清楚的認識。這樣就形成了抱石一生獨特的創作道路,用他自己的話,就是“從生活入手”,“一面從生活入手,一面也不廢汲取傳統的優秀經驗,兩者結合起來。”[4]
自學,不依靠名師,這就使他的創作少受許多清規戒律的拘束,用一句流行的話,就叫作“沒有框框”。由于沒有框框,他的作品就比較自由地發抒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自己的創作方法,這也正是他從石濤那里得來的好處,石濤也從來沒有什么名師指導,而是從歷覽名山大川的生活觀察中從事創作的,石濤自己說這是“天然授之也”。[5]這就是抱石的繪畫藝術特點之一。
“從生活入手”,對于一個山水畫家來說,就是觀察自然界的真山真水,研究它的造型、色彩、樹木、水石、人物、建筑等及其相互關系和各自變化,通過自己的思想感情把從生活中觀察得來的外界感受,用自己的筆墨再現出來。就是用自己的筆墨為題材服務,受自己思想的指揮。(也就是石濤說的:“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6])而不是某些舊文人畫那樣,關在書齋里頭,玩弄筆情墨趣,走向形式主義的死胡同。從生活入手,就擺脫某家某法的桎梏,這是抱石的繪畫藝術的又一個特點。
但是傅抱石絕不是否定對傳統藝術的繼承和借鑒,他自己說得好:“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夠有助于理解傳統;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夠創造性地發展傳統。”[7]對于向古人學習,他也說:“怎樣學習?應當分別來研究,循著他們的道路然后越過他們,是一種;舍本逐末,拋棄他們的發展歷程而僅僅形式主義地追求貌似,這就成問題了。”[8]他這些主張是正確的,他有深湛的美術修養,他鉆研過許多古人關于繪畫心得的著述,也看過許多古代的杰作名跡,但他同石濤的主張一樣,反對簡單的模仿,反對“我為某家役”而主張“某家為我用。”皮毛的模仿,“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于我何有哉!”[9]抱石的畫之所以不同于前人,但又吸收和消化了前人的精華之處,就由于他貫徹了石濤的這一主張。
傅抱石不僅從石濤、程穆倩(即他常在文字中表示傾服的清初山水畫家“江東布衣”程邃)、梅瞿山以至宋元人的山水中吸取對今天有用的方法來豐富自己的筆墨,他還從西洋畫中的水彩技法,從日本的南畫(特別是橫山大觀等)中吸取有用的東西,這些技法或方法,都經過他本人的消化,汰去不適用的東西,融化那些有用的東西,因為結合得渾成恰當,所以不但不覺得格格不入,反而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方法。這也是傅抱石的繪畫藝術另一個特點。
但是,傅抱石的創作道路最根本的一條,可以說是從石濤來的,那就是他經常引用石濤的那句話:“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就是“法自然”。
五、蜀道山川邁步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傅抱石的創作,我請教了南京畫院亞明先生和畫家伍霖生先生,以下的記述主要是我從他們的談話中得來的體會。
傅抱石生長在江西。江西三面環山,山地和丘陵占一半以上。“南昌故郡”一帶“襟江帶湖”,西北也是山林。因此在我國歷史上這個地方孕育過不少著名畫家。五代宋初的著名山水畫家董源就是江西人。明末南昌的八大山人朱耷,不但擅長花鳥畫,山水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飯牛翁羅牧被稱為江西派的領袖。傅抱石從小就在南昌生長,這個物華天寶之都,自然就給他的山水畫打下了基礎。抗戰初期,傅抱石從南京避兵宣城,這里正是石濤和梅瞿山探討創作之地。后來抱石從南昌回新喻故家,不久又從武漢轉湘、桂入川,一住八年,飽飫了峨眉青城、長江嘉陵之勝。這個時期正是傅抱石的繪畫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而四川山水那種氣勢磅礴、變化奇譎的境界,從來就是詩人畫家所流連詠嘆的。抱石對藝術的領會敏銳深刻,加以他那刻苦鉆研的個性,在完全不同于平川矮樹、小橋流水的江南景色的新環境下,就自然而然地開闊了胸襟,從而也就豐富了他的創作意境和創作技法。因此入川時期抱石的作品形成了一個飛躍,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抱石住在金剛坡一帶,屋前屋后莽莽蒼蒼的山林樹石經常是他的創作題材,他有一個時期常常從金剛坡走路走到沙坪壩教課,這一路上山勢回環,江流湍急,這二三十里的跋涉路程,也就是他觀察和構思打稿的過程。大家知道,重慶是多霧的山區,抱石生活在云霧繚繞的山村中,朝夕飽看云山的變化,自然也就深有感受,因此,在傅抱石的作品中,表現奇譎多變的云煙景色是他的特長。國畫水墨山水本來就長于描繪濕空氣籠罩下的風景,而抱石在這方面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這不能不認為是從四川的現實環境中陶冶出來的。所以說,四川的雄偉山川,孕育出傅抱石這支畫筆,并為他后來的發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礎,這是不移之論。
抗戰時期的大后方,人民生活困苦,作為一個有民族熱血和愛國之心的藝術家,自不免于觸目傷懷。傅抱石畫過許多屈原的作品(例如他經常愛畫“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的《湘夫人》)以及杜甫指斥朝政的《麗人行》等“唐人詩意圖”,以寄托其憤時憂國之慨,這也是抱石在入蜀時期的創作風貌。
四川的山川形勢固然使傅抱石的創作開闊了胸襟,但是,拿這一階段的作品和他后一階段做比較,卻還只是像杜甫所說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呢!
六、大江南北筆縱橫
1949年以后,傅抱石的創作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他定居江南,畫過不少江南的平遠景色,但他那時眼底的江南風光,卻絕不同于過去畫家那種柳眼花須,曉風殘月的纖柔意境。而是剛健清新地再現出江南風景的本色。他畫玄武湖、太湖、蘇州、無錫,也都境界寬闊,并且都是根據朝夕陰晴、四時變化作不同的處理手法的。
1957年東歐之行,傅抱石在新的自然風物之前又給自己提出了新的課題,就是如何把西洋建筑和國畫山水技法結合。這本來也是擺在許多現代國畫家面前的共同課題,但是傅抱石卻解決得渾成自在。他在日本留學時本來就有些西洋畫基礎,同時他的國畫技法又是“從生活入手”的,因此對于外國風景的表現,就并不困難。《布拉格之春》這幅畫是他自己較滿意的作品。
1959年9月《江山如此多嬌》的創作,又給傅抱石提出另外一個新課題,這幅空前大幅的畫,在國畫史上還沒有人畫過,表現技法上固然需要不斷摸索,就是工具也得重新設計——大筆和排筆的桿子就有一米多長,像掃帚一樣,調色用大號面盆,一擺就是五六個。而探索主題、經營位置……也都是綜合了很多人的意見再由抱石和關山月執筆的。這個新課題的完成,使他深深感到一個道理,集體智慧是巨大的藝術創作最好的保證。
1960年秋的二萬三千里旅行寫生,又給予傅抱石的繪畫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古代的山水大家,本來都是經歷許多名山大川,從中得到豐富的題材和技法的。石濤說:“盤礴睥睨,乃是翰墨家生平所養之氣。”“氣”如何“養”?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是十多個畫家,有組織有目的地為了畫畫去游歷兩萬多里的山川,這在以前是辦不到的。效果呢?用傅抱石自己的話,叫作“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傅抱石這個時期的作品,確實又在本來的淋漓恢廓基礎上,更加上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渾厚奔騰的氣質。他畫了許多面貌一新的山水畫,例如《黃河清》《紅巖》《棗園春色》《西陵峽》等等!這一次壯游,使江蘇畫派產生了新面目,使傅抱石本人的創作,又產生一個飛躍。
但是,傅畫的造詣邁進到另一個新高峰,則是他在1961年夏的東北之行,這一次他到過許多地方,畫了鏡泊湖、天池、長白山等關內沒有的雄奇山水。回來以后,抱石興致勃勃地對我說:“前人早就說過,山水畫的皴法是從畫家接觸到的真山真水中體會出來,而不是畫家為了好看,就能在畫室里憑想象把‘披麻’‘解索’畫出來的。這次到東北,使我見到東北許多山水的形質奇詭,絕不是過去的‘斧劈’‘披麻’……所能表現的,原因是我國過去的畫家由于條件的限制,足跡很少到過關外,他們未見我國東北部山川的面貌。因此我到了長白山和鏡泊湖等地,親自感受到那里的水石嶙峋,使我悟出新的皴法來。我主張畫家們今后多到東北寫生,這就會給國畫開辟一個新的境界。”的確,我們看到他的《天池飛瀑》《林海雪原》等作品,感到傅抱石的面目又為之一變,東北山水對傅抱石的晚年作品確有很大的影響。
1950年以后的山水畫家傅抱石,就是這樣以大江南北的壯麗河山滋潤他的如椽之筆,因而他那辛勤的藝術勞動也就使豐富多彩的中國山水畫史添上鮮麗的一頁。
七、意境創造筆墨
傅抱石作畫,愛用勁毫破筆,用舊了的狼毫筆是他最得力的工具,他一般愛用較大的筆。但根據不同的情況,用柔毫小筆作畫也不是沒有的。
熟朋友都知道傅抱石是愛用皮紙作畫的,這也正是他戰時在四川養成的習慣,那時宣紙價高難得,皮紙則是四川的土產,供求方便,抱石用慣了,掌握了皮紙的性能效果,從此也就大量用它。直到今天,江蘇畫派的許多畫家,在他的影響下,也都愛用皮紙作畫。
傅抱石的山水畫和傳統的山水不同,他注意到自然界不同季節、不同氣候的變化,在他的作品中,春夏秋冬,晴、雨、風、雪的表現,晨、昏、午、夜等光景的區別,都十分鮮明。試拿雨、瀑布和海的表現來說,傅抱石在國畫技法上都有新的貢獻。他畫雨景用灑礬和排筆渲染(畫瀑布有時也用此法,參看《江南春雨》《天池飛瀑》兩圖)。畫大海和瀑布,在渲染之外,有時用干皴來表現波濤起伏和奔流澎湃之勢。畫山石,勾、皴之外還加重墨濕染來現出山勢的郁蒼。由于傅抱石要求畫面充分表現出自然界的各種變化,因此渲染技法,也就必然要求有新的創造。
不但渲染,在傅畫中皴法也卓越地發展了傳統技法。懸崖陡壁,他愛用劈頭蓋面的斫筆皴,回環山勢,用圓轉近乎打圈的卷云皴。他有時也用斧劈和近似黃鶴山樵的牛毛皴,但這些皴法都不全同于過去的形式,抱石往往根據山形土質的需要創造出許多無名的皴法,我們見他畫山,有時長線斜下,再疏疏地用飛白勾出些曲線、破圈形的山石紋路,這種皴法似乎隨意,但極謹嚴,恰當地表現出土石的立體感。他的這些無名皴法,江蘇的畫家給它起個名字叫“抱石皴”。
線條、皴擦、渲染和苔點是國畫的基本技法和基本構成因素。苔點的運用,從米芾到元四家已表現很高的造詣,石濤更是發展了前人的點法,達到了高峰。傅抱石從石濤的作品中體會了苔點的妙用,他更熟練地使用“破筆點”畫樹和苔蘚。他愛在山石中用一部分破筆點,以增加畫面淋漓蒼勁的氣氛,更加表現出自然界的欣欣生意。傅抱石的苔點技法是從大自然的觀察中提煉出來,而又恰好地表現大自然的氣勢。和他的皴法緊密聯系和配合,以構成他特有的風格。
傅抱石在國畫技法上的貢獻不是這一短文可以詳盡介紹的。例如他在用線和用墨方面都有湛深的研究,他的線條(筆觸)凌厲飛動,喜用禿筆長線,有時則用草書筆法作皴。墨更是抱石在山水畫上淋漓痛快地發揮的技法。他認為在我國中世紀,墨是隨著山水畫的飛躍發展而顯其重要的。他從傳統技法中看出“墨即是色,色即是墨”這一水墨技法的竅妙。在他的作品中,有時濃重的“潑墨”使用得十分恰當(特別是表現森林或高山叢林)。這些都是他在傳統技法的繼承和發展上做出的貢獻。
一切技法都服從于意境,意境是作者對于客觀描寫對象的感受和取舍加工。作者決定了描寫對象,經過深入的思考選擇,突出主要部分,汰去次要和冗雜部分,構成初步的方案(其中包括布局、構圖、主調等等),使之比真實情景更高、更集中、更藝術化,這就是意境。畫家作品的優劣,往往取決于意境的高低,而意境的構成,既依賴于畫家對客觀事物的感受,又依賴于技法的掌握運用。傅抱石的寫生作品,首先是用線條簡略地記下印象,第二步是把記下的印象經過加工整理,初步擬出一個輪廓,然后進入第三步,則是較仔細地構成定稿。這時他胸中有了“丘壑”,有時先用木炭在畫紙上勾出位置,(中國畫的專用詞叫做“圬”)有時卻不在紙上起稿,而是直接用水墨畫在紙上。抱石在畫室作畫,根據傅夫人的回憶,是很有意思的,傅夫人說:他習慣于將紙攤開,用手摩挲紙面,一邊抽著煙,眼睛看著空白畫紙,好像紙面上就有什么東西被他發現出來似的,摩挲了半天,煙一根接一根地抽,忽然把大半截煙頭丟去,拿起筆來往硯臺里濃濃地蘸著墨就往紙上掃刷,他東一下西一下地刷得紙上墨痕狼藉,使旁觀者為之擔心納悶,可是他胸有成竹地涂抹著,涂到一定程度,就把它掛在墻上,再坐下來抽煙,但仍然目不轉睛地全神注視著墻上的畫。然后取下來放在畫案上渲染層次,添補筆墨,畫中的山川景物逐漸具體,還是反復地掛墻、卸下、細察、冥想,有時滿紙淋漓,拿都拿不起來。待它稍干,然后做最后一道細致的“收拾”(添補部分細節)功夫。他的畫大處淋漓奔放,小處精細耐看,就是這樣產生來的。傅夫人的這段精細而真實的描述,說明了抱石作畫追求意境的構思,是十分艱苦的勞動。每一幅畫由于意境不一而呈現不同的表現技法。同時,由于畫家創作意境的日益提高,熟練精妙的皴染點線等技法,也就層出不窮了。
八、著述·篆刻
抱石匆匆60年的生命,卻給藝術界留下可驚的成績!他不僅是個畫家,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他還是一位美術史家和篆刻家。
大家都公認,在我國歷史上,畫家而有豐富的美術著述留傳于世的,應以近代的黃賓虹為首屈一指。而后來居上的傅抱石更是大大地超過了他。傅抱石的著作和譯述,30年代以來,就深受讀者重視。其中如《中國繪畫理論》《中國美術年表》《中國的繪畫》《中國的人物畫和山水畫》和《唐宋之繪畫》(譯自日本金原省吾原著)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在抗戰時期的重慶,他在條件十分困難之下寫成了《石濤上人年譜》,盡管近年來關于石濤的材料,有許多為作者當時所未見的,但這本書至今還是關于石濤研究的重要著作,今天許多研究石濤生平的著作,都以他這本書作為研討的根據。傅抱石在中國美術史研究方面,簡明扼要地歸結為“從主題內容看,五代以前以人物為主,元代以后,以山水為主,宋代是人物、山水的并盛時期;從表現技法看,五代以前以色彩為主,元代以后,以水墨為主,宋代是色彩、水墨的交輝時期。”[10]他認為中國的山水畫發展,就其體現祖國自然的偉大美麗來說,“是基于現實意義的發展,是進步的”。但17世紀以來的形式主義傾向,卻籠統地說山水、水墨、寫意就是中國畫的全部傳統,這是錯誤的,山水畫盛行以前的基于現實主義精神的人物畫,同樣是我國繪畫的光輝傳統[11]。基于這個結論,他認為繼承和發揚國畫傳統,兩者是不能偏廢的。他還對我說過,有些美術史家認為宋以后中國封建社會由極盛而日趨衰落,因此,美術也逐漸式微,這種說法是機械唯物論,從我國美術發展的長河來看,水墨畫和山水畫的出現,并不就是美術日漸衰落的表征,只能說,這是河流的一個拐彎,對奔流的河水來說,并不妨礙它的前進。這個見解,是發人所未道的。
傅抱石對于中日文化交流,也做出過貢獻,他早年介紹不少日本學者關于中國美術的論文,他也給中國介紹過雪舟等楊等日本古代畫家的成就。他為了把中國山水的皴法加以科學的整理,曾經做過一番努力。他從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深刻地體會宋代郭熙所說“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林泉高致》)的意義,要向真山水學習,就要有起碼的地質巖石知識。他深知古人的皴法是從對大自然狀貌的細心研究中得來的。后來他發現日本高島北海寫過一本《寫山要訣》,也正是從長期的地質調查考察中,發現中國山水畫皴法的創造性和科學性。他覺得這本書對于科學地整理和促進我國山水畫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就把它翻譯出來,這本書的問世,使今日許多從事山水畫研究的人得到啟發。
1950年后,傅抱石還寫過不少論文介紹一些前輩畫家的成就,以供后學參考。他給《鄭板橋集》寫過一篇前言,詳細地評介這位卓越的清代藝術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他寫過《白石老人的藝術淵源初探》,全面地介紹齊白石的藝術成就。在他的晚年,還寫過很多創作經驗談——《畫室有感》《江山如此多嬌的創作》《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東北寫生雜憶》等文章,以誠懇而謙虛的態度,把自己的學問心得向讀者盡情介紹,使藝術青年從這里吸取營養,得到借鑒,絕沒有過去藝人“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的那種保守觀念,這些都是抱石孜孜不倦地為我國美術的繁榮發展所做的工作。
上面已經介紹過,篆刻是傅抱石很早就愛好的一門藝術。他年輕時候一味模仿趙之謙的《二金蝶堂印譜》,但他在經過了長期的艱苦歷程之后,得到的結論是:“刻印不比學畫,畫可搬而印不可搬,畫可不斷臨摹而印必須獨創。”[12]獨創是傅抱石對待自己藝術創作的一貫態度,不但他中、晚期治印是如此,我們從上文已經知道,他的作畫態度也一貫如此。但是獨創并不等于閉著眼睛蠻干,他解釋“獨創”或“膽敢獨造”的含義是“既嚴肅認真,有典有則,而又奇兵突出,妙著頻生”。他完全同意齊白石不死摹古人形跡而又十分尊重傳統的辯證主張。他對于專攻漢印或周秦小璽,或只鉆研甲骨、金文……等而下者則抱著一部《說文解字》刻一輩子,守著《六書通》《六書分類》討生活,這些壁壘森嚴、各立門戶的做法,絕不贊同。他主張涉獵所有的古印碑版,從中接受有益的影響,他更傾心漢印,認為漢印比秦印更活潑、更有創造性。他所刻的白文印,有很多漢印的氣息,但他反對生吞活剝,生搬硬套。他還同意利用隸書、楷書入印,這些都是他所謂的“獨創”。傅抱石在留學日本時代,他的篆刻很受到彼邦人士的重視,大約在1935年上半年,《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都有關于傅氏篆刻的報道文章,那時上海《良友》畫報也轉載過。
傅抱石認為刻章的首要之圖是書法(篆法)的鉆研,他說:“篆刻是以書法為基礎而結合雕刻加工的藝術。”[13]傅抱石的書法也是造詣很深自成一格的。他以石鼓的形式寫小篆,這種風格常常在他的題畫中看到(并且和他的畫風十分統一)。而由于他的篆刻功夫,書法也更遒勁,行楷的氣韻含蓄,也同樣看出湛深的功力。
抱石晚年因為眼力不好,就很少刻印。但是那個時期他的功力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確實做到了打破“浙派”“皖派”,漢印、金文這些框框,也不是近時流行的吳昌碩、齊白石一派,而形成了他自己獨有的風格,“當驚世界殊”“換了人間”“往往醉后”“不及萬一”都是他晚年自刻的畫角用章,從這里可見其篆刻成就之一斑。
九、永遠被人懷念
傅抱石是一個誠篤樸實的藝術家,他對自己的藝術創作嚴格要求,平常總是工作到深夜。可以說,從他上學讀書時代開始直到他的晚年,都一直在勤奮工作中度過的。
傅抱石對朋友和學生總是一片熱情,并且不論在得意還是失意之際,待人接物都一貫地殷勤懇摯,他受過別人一點好處,都終生不忘。平日寧可自己生活刻苦,總是照顧比自己困難的同事和朋友。他的這種性格和徐悲鴻很相像,他們兩人都同樣出身于貧苦家庭,同樣在他們的青春年代由于自己的努力和朋友前輩的幫助,逐漸向成功的道路邁步,也同樣具有中國知識分子那種可貴的正義感。平日平等待人,同樣沒有所謂“藝術家”的架子。這些都使朋友們感到他們兩人有共同之處。此外,以今天的環境條件來說,他們都未享高齡,正是由于這一無可彌補的遺憾,使我們感覺到他們兩人的成就高低、風格意境盡管不同,而拿齊白石、黃賓虹的壽命和造詣來比,就同樣都有花朵還沒有等到盛開就已匆匆凋謝的無限惋惜!
至于在個人生活上自奉甚儉,這也是徐、傅兩人的共同特點,所不同的就是徐悲鴻不愛煙酒,而傅抱石則與杜康結不解緣,在創作的時候不停抽煙。但衣食住行方面他們都十分隨便。所以在重慶時人家說傅抱石“名士派”,其實這種隨便并不是什么藝術家或名士風度,而是他從小養成的生活簡單的習慣。
但是作為一個畫家,他對于創作工具的搜求卻并不吝嗇,他作畫并不局限于使用國畫顏料,同樣也搜購國內外的優質水彩和粉彩顏料以供揮灑。他和關山月在北京創作《江山如此多嬌》這幅巨制,用了近百張乾隆“丈二匹”,等他畫畢回南京時,他還不惜以60元一張的代價,買了一批帶回去。
傅抱石的酒量是有名的,他作畫時,正如他自己刻在圖章上的那句話——“往往醉后”。晚年由于高血壓和心臟病的關系,醫生堅囑戒酒,家里也給予一定的限制,那時酒興也不如以前。記得1952年,他對我談起在重慶金剛坡時的一件趣事:大約是有一年除夕,他晚飯后開始喝酒,一面喝一面攤開畫紙繪一幅山水,畫到深夜,他覺得這一次畫得非常成功,山巒云樹的皴染得心應手,而且層次越染越分明,大幅度的潑墨更是淋漓盡致得未曾有,于是他就在天明前入睡了。醒來睜開眼睛第一件事,自然就是要看看自己這一幅“生平得意之作”,可是真怪,桌上沒有,墻上也沒有,椅上、地上到處找,都找不到,一連幾天他都為這幅“杰作”的失蹤痛苦懊惱,他并不像顧愷之那樣相信這是“神物飛去”,還始終念念在懷。忽然有一天他在打掃衛生時,在蚊帳頂上發現了這幅畫,原來已經在那晚大醉之后涂抹成黑墨一堆,被他摶成一團拋到床頂上去了。
傅夫人羅時慧女士,無愧于傅抱石的畢生知己,她學識廣博,能詩詞。對傅抱石的作品有精深的了解。她不僅在解放前艱難的日子里肩負了生活的重擔,對兒女的教育也替抱石分擔了許多憂勞。她還是抱石精神生產的親切助手,抱石作畫喜用大量的濃墨,她就長期負擔這個磨墨的工作。傅夫人最近給我的來信中,還風趣而謙虛地自稱為傅抱石的“磨墨婦”,其實便在這磨墨的過程中,傅夫人也就是傅抱石的創作參謀。1961年傅抱石在東北畫的《林海雪原》,反復思索想不出恰當的畫題,還是傅夫人給他想出來。傅抱石在這幅畫的題識上,就記下了得題的經過。傅抱石有二子四女,有好幾個兒女,在繪畫上都看得出將是繼承父業的鳳雛。
1965年春天以后,傅抱石就被醫生一再警告,由于高血壓和心臟病,他必須防止過分勞累。那年9月底,上海民航公司派專機邀請他到上海去計劃給國際機場的大廳作畫,他因為是短途旅行,便欣然同意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是9月28日,他仍然像往常一樣起得很早,沿著漢口路寓所的花園山徑下去散步,也像往常一樣在八九點鐘就回到樓上書房,習慣地躺在大搖椅上小睡。那時傅夫人正在樓下會客,大約10時左右,忽然聽到樓上發出一聲異常巨大的鼾聲,傅夫人急忙上樓去察看時,我們這位為中國藝術辛勞了一輩子的傅抱石先生,已經由于心臟病突發,默默地和他熱愛的祖國、熱愛的山川草木、熱愛的親人以及他的藝術愛好者們永別了!
中國的山河大地日益壯麗美好,文化藝術也將日益繁榮昌盛。這個曾經在那里生息過,以自己的心血灌溉過這塊藝術園地的中國人民之子,也將永遠被人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