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澄漫無目的地在大街上走著,直到人行道對面閃爍的綠燈變換為紅色,旁邊的男人出聲提醒,她才停下腳步。
“需要幫忙嗎?”男人關切地問。
“不用,謝謝。”溫澄淡淡地道謝,冷漠的回應讓男人望而卻步。
十點,少了上班高峰期的車水馬龍,浦淞的街漸漸安靜下來。溫澄靠著記憶里的地圖,繞過兩三條安靜的老街,看著梧桐樹下的老式紅磚洋房,終于上前一步,摁響門鈴。
這里是浦淞市一處充滿歷史的長街,大城里鮮有這樣寧靜愜意的地方。溫淵最常居住的一所老式洋房就坐落在這里。
須臾,開門的是一位老婦人,她推了推老花鏡,仔細辨認眼前敲門的人,猶豫道:“是七小姐?”
聽見這個稱呼,溫澄一頓,隨后頷首問道:“您好,請問溫淵在嗎?”
“溫教授在的,”老婦人在照片上見過七小姐,于是把溫澄迎進來,“您隨意,我這就請他下來。”
老婦人上了一杯熱氣騰騰的英式紅茶,便慢吞吞地上了樓。
溫澄沒有坐下,她站在壁爐前,注視著壁龕上立著的兩幅原木相框。
正在她發呆的時候,視線里一只寬大的手拿起其中一幅相框,聲音低沉道:“這是慕卿和她的母親周氏。”
陳舊的照片里,溫慕卿還是個襁褓中的嬰兒,抱著她的周浣玉眉眼溫和,穿著一身頗具江南風情的雅致旗袍,身后站著年輕時候的溫淵。
沒被拿起的另一幅照片,則是溫淵和陳清的合照,照片里一共五個人,除了西裝革履的溫淵,其他四人都是年輕裝扮,看起來似乎是他的學生。前排是兩個身材嬌小的女生,后排的陳清和另一個健壯男生站在溫淵身邊,一左一右。
“這是你母親,當年她在學校里與這三個人的交情頗深,我所教的課程結課之后,他們找了攝影師拍照留念,”溫淵不緊不慢地介紹著照片的來歷,“他們三個人,如今一個在外交部,一個在翻譯局,這一個移民加拿大,不過這些年沒什么往來。”
他說話間,溫澄已轉身離開壁爐前,在沙發上坐下。
溫澄臉上沒什么表情,冷冷淡淡的,目光落在桌子上的骨瓷杯上,瓷杯上的花紋素致淡雅,晶瑩剔透。
“今日怎么突然來找我?”溫淵瞇著眼,若沒記錯的話,昨天父女倆才剛見過面。
溫澄開門見山就說:“你以前從沒告訴過我,溫山和祁家的事情。”
溫淵一頓,露出薄笑,反倒回她:“你也從來沒問過我。”
隨后,他臉色正經道:“溫山和祁建輝是上一輩的事情,難道還會影響到你和那小子。”
“你知道?”溫澄抬眸,目不轉睛地盯著溫淵,問道。
溫淵坐在她的斜對面,兩只手交疊成塔狀,搭在膝蓋上,“多少知道一點,他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都在新加坡國大,當時可以算是好兄弟吧。”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祁家在新加坡投資了一家石化公司,那家公司出了一次嚴重事故,溫山沒有出手相救,反而迅速撤資,讓祁建輝去處理一堆爛攤子。祁家是傳統的家族式企業,決策決議都要經過擁有股權的家族長。后來,祁建輝因為這一次投資失敗,落魄回國,白手起家。新加坡的祁氏則被他的堂弟祁建英全面掌控,起初發展很快,祁家的產業已經能達到新加坡石化市場份額的30%。”溫淵的語氣平平,他緩了一口氣,接著說,“可惜市場發展速度越來越快,競爭愈發激烈,這種企業形態的弊端就會顯露出來。”
“創業初期,決策的高效率和果斷性,是家族式企業成功的重要保障。可隨著蛋糕越來越大,祁家的內部組織機制出現問題,發展方向也遇到了瓶頸。”溫澄補充道。
溫淵向她投去贊賞的目光,補充道:“沒錯,這個時候,祁建輝在國內已經有了自己的根基,他底下的人,通過成為祁建英的職業經理人,幫他獲得了不少內部消息。后來,祁氏因為賬款管理不善導致現金流緊張,陷入財務危機。通過祁建輝的牽線,祁氏獲得了一筆戰略投資,度過危機。”
“從那以后,祁建英就失去了對祁家的話語權。祁氏,又回到了祁建輝手上。”溫淵含笑看著溫澄,“你當時還小,應該沒什么印象。”
溫澄恍然,她記得有一年的春節,祁家回新加坡過年,祁琚整整消失了一個月,毫無音訊。
那個階段,大概就是祁家權力更迭的時期。
“所以,你今天是見了祁建輝?”溫淵啖了一口茶,透過杯子里的熱氣看他這個心事重重的女兒。未等到她的回答,但溫淵心里已經對溫澄和祁建輝之間的談話內容知道了個七七八八。
溫澄的思維飛速運轉,聽完當年的故事,她總覺得溫淵在故意隱瞞了什么,直到她看到溫淵放下茶杯,手重新放在膝上,溫澄才想起來她最初疑惑的地方,“溫山的腿是怎么傷的?”
“嗯?”溫淵想了想,補充說,“溫山的腿,是被祁建輝的姐姐,祁嵐撞斷的。”
溫澄沉默,“他們.......”
“祁建輝失意的那段時間,他的母親,也是祁嵐的母親,因惡疾沒有及時得到治療,很快去世了。”
“可為什么,祁嵐要撞他?”如果只是因為生意失敗,溫山沒有出手相救,祁嵐會因為這件事撞斷他的腿嗎?
溫淵一笑,微微舉起手中的茶杯,神情有些無可奈何,“小七,你還沒明白其中緣由嗎?”
沒等溫澄說話,他又笑著慢慢說——
“溫山這個人呢,曾經一度被老爺子當成未來接班人培養,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手段陰險狠辣。當年,他和祁建輝稱兄道弟,不過是想要通過祁建輝滲透祁氏。而祁嵐這個女人,則是溫山靠近祁建輝的第一步。但他逐漸發現,祁建輝的能力遠遠超過他想象,根本沒辦法為他所掌控,于是他找到了下一個傀儡,祁建英。”
“那次擊垮祁建輝的石化事故,并不是祁建輝底下的人疏忽導致,而是溫山故意設下的局——把祁建輝踢出局,讓祁建英上位。祁建輝能力雖有,卻太容易相信別人,直到溫山撤資的那一天,祁建輝還以為溫山是受到老爺子的逼迫,才沒有出手救他。自那以后,祁嵐對溫山也沒有了價值,而惱羞成怒的人,往往容易做出極端的事情。”
“溫山的腿,大概是他玩弄祁嵐感情的報應吧。”
聽完溫淵的話,溫澄感覺自己的心正猛烈撞擊著胸口,一直纏繞在她心頭的那些困惑,隨著溫淵的談述逐一解開。
“你當年找到我的時候,就知道我和祁琚的關系。”溫澄低下頭,嘴角微動,拉扯出一個勉強的角度。
溫淵看著她愈發蒼白的臉,搖了搖頭,淡淡地道:“起初,我只是知道你與他的關系很好。后來我才從老爺子口中知道,原來祁家與溫山還有那樣一段糾葛,至于你和祁琚之間,我想老爺子應該有所打量。”
再抬起頭時,溫澄已經理清所有思路,神情也恢復如常,她道:“在你們眼里,我和祁家的關系,是可以拿來打壓溫山的籌碼,對嗎?”原來在程家的那些時光,她已經作為一顆棋子,被安放在了應該在的位置。
溫淵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反問她,“你知道,老爺子是為什么注意到你的嗎?”
溫家子孫眾多,溫淵沒有摻和溫家的生意,膝下只有一個女兒,本就是不起眼的一房。起初,溫思儉并沒有對溫淵流落在外的私生女有什么想法,但后來,他卻主動和溫淵提起,要讓溫澄回到溫家,入了族譜。這也是溫澄一直疑惑的地方,是什么讓溫思儉這只老狐貍主動認回自己?難道真的和祁家有關系?
溫澄搖頭,“不知道。”
“那年你在陽春縣,以岑讓威脅岑志忠的事情,老爺子很快知道了,”溫淵解釋著,“你從下晝路中學轉回滎城的高中,也是老爺子安排下去的。”
怪不得她當年回來得那么順利,無論是學籍,還是手續,沒有任何阻礙的讓她回了滎城。
溫澄忽地笑了,喉嚨一澀:“我不明白,我就這樣得了老爺子的眼光?”
“你很聰明,在那個年紀就知道如何抓住別人的把柄為自己爭取最大的利益,懂得隱忍不發,善于洞悉人心。老爺子曾經在我面前稱贊過你,這像一個真正的溫家人。”
“所以,溫思儉在我身上花費那么多力氣,不僅因為我能替他身先士卒,還因為我和祁家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制衡溫山,是嗎?”溫澄靜靜地與溫淵對視,聲線異常的冷——“如果我和祁琚在一起,以祁建輝和溫山那些過往恩怨,祁家絕對不可能支持溫山,更有可能幫我打壓大房。而溫峙所掌控的股份并不多,也威脅不到任何人。所以,最后的贏家,就是溫渟。”
溫淵沉吟,許久才道:“所以,這就是我不想你進溫建的原因,你斗不過那幾只老狐貍。”
溫澄自嘲一笑,站起身頭也不回地離開,路過壁龕時,她看著照片里陳清粲然的笑容,說道,“可惜了,祁建輝說了,他不會接受任何一個溫家人。我不可能得到祁氏的助力,也不會拉祁琚下水。”
……
聽見大門合上的聲音,老婦人又從樓上慢吞吞地走下來。
她摸了摸茶杯,還是滿滿的茶水,已經涼了。
“您這個女兒,似乎是很不省心呢。”她自言自語道。音量不大,但溫淵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溫淵收回看向大門的視線,不被人察覺地搖搖頭:“還是太年輕了。”
“雖然年輕,但很聰明、堅韌。依我看,七小姐和祁家少爺的關系斷不了。”老婦人添上一杯熱茶,“她今天知道這些殘忍的真相,或許就能早點退出溫家的紛爭之中。”
溫淵嘆一口氣,看向壁龕上的照片,聲音變得有些飄忽:“我做的這些事情,阿清應當不會怨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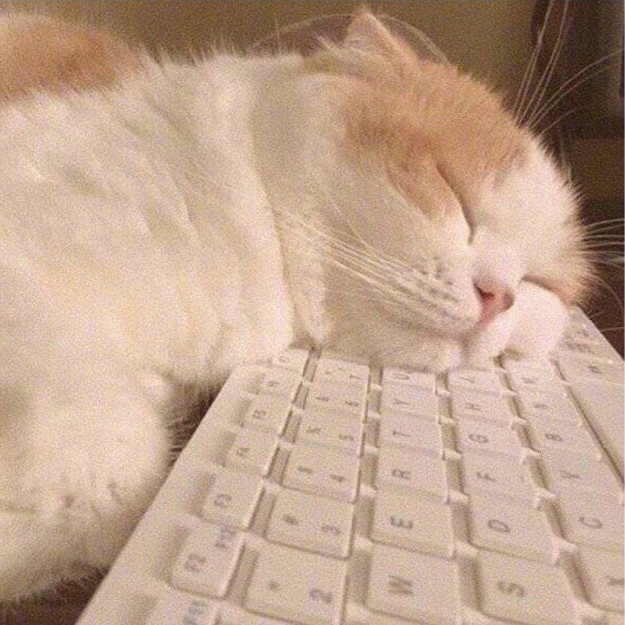
浮沸
放心,沒有“給你一百萬離開我鵝子”的戲份,畢竟溫澄抬手也能賺到這么多錢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