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后悔,恐懼……
蔡寧被負面情緒所包圍著。
這不是一種美好的體驗,從頭皮到腳底,每一寸肌膚都在顫抖著。以至于身上傷口所帶來的痛苦都算不得什么了。
如果有可能,蔡寧肯定不會和洛陽去找張二爺的麻煩。
他的母親辛辛苦苦地養育了他二十年,從記事起,身邊就只有母親。
本想著當了捕快,就能讓母親過上好日子了。
事實上,娘倆兒現在的日子確實比以前好過的多了。
可現在因為自己,牽連到了母親,這是他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安靜地地牢內,墻壁上燃燒著的油燈不斷飄搖著。
“嗒。”
“嗒。”
緩慢地腳步聲打亂這份壓抑的寂靜。
蔡寧猛然抬起頭,看向拐角的樓梯處。
狹長的影子在石頭堆砌而成的墻壁上游動著。
是誰?
年輕捕頭的心臟已經提到了嗓子眼,生怕下一刻看到自己年邁的母親站在自己面前。
那是一只素色的繡花鞋,順著鞋子向上看去,鞋子的主人是一名十六七歲的女子。
看著對方眼角的淤青,蔡寧知道對方不會是來救自己的。
松了口氣,蔡寧再度低下了他的頭顱。
雙手扶著墻,踩著石梯,少女搖搖晃晃地走來。
喘息粗氣,停在了蔡寧身前。
“蔡,蔡捕快。”怯生生地聲音中,滿是痛苦與疲憊。
蔡寧沒有回應的意思。
“捕快大人?”說著推了推蔡寧。
被那只手按住的地方,入骨的疼痛傳來,蔡寧瞬間清醒了過來,“嘶,我去你大……”
“啊,我……”慌亂中,女子連忙收回手,借著昏暗的燈光看去,粘稠的黑色液體沾滿了那只素白的小手,“我,對,對不起。”
實在是沒力氣罵人了。
“你……”
“我,我叫小荷。”如同做錯事的小孩子一般,細長的手指在身前不斷纏繞著。“我來救……”
“好,你叫什么無所謂。”蔡寧吸了口冷氣,“你去讓張二爺下來,他要問什么,我都說了。”
既然派人來了,那就說明自己在張二爺心里還有用處。
只要還有利用價值,那就還有商量的余地。
“啊?”意外地,自稱為小荷的女子,臉色瞬間慘白,難以置信地問道,“都,都說了?”
“這不就是張二爺派你來的目的嗎?”蔡寧自嘲道,“去告訴他吧,我都說。”
沉默……
就在蔡寧快要失去耐心的時候,小荷終于鼓起了勇氣,“你,你不是捕快嗎?”
“廢話。”蔡寧沒好氣地說了一句。
“捕快怎么能向他那樣的人妥協?”胸脯劇烈起伏著的小荷死死地盯著無法動彈的捕快。
小荷有許多話想說,可她嘴笨。
但是她依舊想問一問,為什么捕快會是這樣的軟骨頭。
明明自己下了好大的決心,才悄悄地來到了這里。
小荷的想法很簡單,把這名捕快救出去,那么自己也有了逃出生天的可能性。
張二爺不會放過她的。
他們商量事情從來不會避開自己。
她不傻。
她知道這不是信任,就好比家里養了一只寵物,討論大事的時候會刻意避開寵物?
不會的,寵物就永遠只是寵物。
喜歡的時候,好吃好喝的供著,性情不好的時候,一腳踹開就是了。
而知道張二爺這么多事以后,被踹開的時候,就是她生命走到盡頭的那一天。
小荷無數次在夢境中見到那一張張慘白,膨脹變形的臉。
小荷知道,那可能也是她的下場。
她不想死,所以她來到了這里,來救這名捕快。
可希望才剛剛露頭,就被對方一句話無情地拍死。
這甚至比一直處在絕望中更令人絕望。
若是連代表公正的捕快,也向魔鬼低下了頭,那么誰又能救自己呢?
短短的一瞬間,小荷仿佛老了十歲一般,整個精氣神頓時垮了下去。
而一旁不明就里的年輕捕頭只是催促著她,讓她去找張二爺。
對于蔡寧來說,只要母親安全,那他什么都可以出賣。
“愣著干嘛?”蔡寧咬著人,惡狠狠地問道。
小荷看了他一眼,覺得好累好累。
于是機械地轉過身,向著來路走去。
“喂,你……咳咳。”情急之下,牽扯到了傷口,咳嗽聲頓時響起。
“求求你,咳咳,不,咳咳,不要走,咳咳。”仿佛要將肺給咳出來一般,蔡寧看著小荷的背影,賣力地呼喊著。
在蔡寧的注視下,小荷終于停下了腳步。
扭過身,麻木地看著蔡寧。
“求求你,幫我把張二爺找來。”
“求求你,我有話要說。”
“告訴他,我有洛陽的秘密,他回頭肯定會給你賞賜的。”
“求求你,求求你。”
昏暗的地牢中,男人重復著自己的請求。
漸漸地,請求聲變成了嗚咽聲。
而后痛哭流涕。
壓抑的哭聲在地下深處回響。
看著卑微如狗,只會賣力的求著自己的朝廷捕快。
小荷笑了,笑的有些悲涼。
“好。”小荷點了點頭,最后看了看年輕的捕快,轉身走進了油燈照不進的陰影中。
她的身后,傳來狂喜的道謝聲。
若是平時,蔡寧或許還能從小荷的臉色中看出不對勁的地方。
可是現在他心中只想著如何護住自己的娘親。
所以他沒有心情再去觀察這名同樣遍體鱗傷的女人。
……
當洛陽離開了那座老舊的小院之后,蔡楊氏又在自家院子里等待了一個時辰。
入夜之后,她的兒子依舊沒有回來。
收起了針線后,這名婦人來到堂屋中,點燃了三炷香,恭恭敬敬的插在了香爐中。
蔡楊氏不識字,但是她知道每一塊牌位上寫的是什么。
她的目光落在了最下面的那塊靈牌上,“我們兒子出事了。”
“你個當爹的不看著點自己兒子,我也拿你沒辦法。”
“可他也是我兒子,那我就自己想辦法。”
“這要是做錯了什么事,你可怪不得我。”
“我這都是為了你老蔡家的香火。”
說完這些話,婦人離開了堂屋,走出了院子。
……
千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
“阿嚏。”強烈的噴嚏聲在雪原之上響起,驚起數頭覓食的雪兔。
“轟。”一道黑影從雪地里鉆出。
隨意地擦去鼻涕凝結而成的冰碴子,通體裹著白布看不清面貌的男人不自覺地轉身,僅剩的那只手搭在眉間,看向南方,小聲嘀咕了一句,“咋的了?”
……
洛陽終究沒有讓王捕快一個人闖入這座小院。
看了眼洛陽身后,那鐵塔一般的漢子,這名當了二十余年捕快的漢子,微微愣神。
“常大?”語氣中滿是驚訝。
看了看目瞪口呆的王德,又扭頭看了看一臉憨笑的常平,“你們認識?”
“認識。”
“不認識。”
兩人同時回答了洛陽的問題。
低頭仔細打量了一圈王德,常平再次重復了一遍自己的答案,“我不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我認識他。”王德收回視線,接著,微不可察第嘆了口氣。
“你去找將捕頭了?”
“嗯。”看來王德真認識這個傻大個。
“常平,你在這兒蹲好,不要亂跑。”沖著常平說了一聲后,洛陽向王德使了個眼色,向一旁走去。
“什么情況?”
王德心說我還想問你呢,“你怎么把這個傻大個找來了。”
“我找了好些人,只有姜慶派了個人手給我。”洛陽說著,側身看著遠處墻角下,老實蹲著的大塊頭,頭也不回地問道,“他那里是不是有毛病?”
說話間,手指著腦袋。
“嗯。”王德應了一聲。
“那他怎么當上捕快的?”洛陽有些詫異,雖然不太清楚衙門里任職體系,可這種憨子怎么成為捕快的。
“誰說他是捕快了?”王德翹著屁股,小心翼翼地看了過去,發現常平正沖著自己的方向傻笑,連忙收回頭。
對啊,誰說他是捕快了?
洛陽認真想了想,還真沒人說過,也就常平和自己討論了一下他口中的牌牌的差異。
就這,到現在也沒討論清楚。
“所以他真是捕頭?”洛陽更加好奇了,難怪他非要說兩人的牌牌一個樣。
“誰跟你說他是捕頭了?”或許是蹲著的緣故,又或許是天色的原因,王德此時似乎放開了些。
“有話直說,賣什么關子?”洛陽沒好氣地瞪了王德一眼,只可惜王德看不到他的眼色。
“他是衙役。”王德頓了一下,“其實也不算衙役,就是有一把好力氣,就留下了他,給他口飯吃,帶著他去巡邏啥的,抗點東西也方便。”
“那牌牌……”洛陽本來想說的是銅牌,可是剛才和常平別了那天,給整口胡了。
“哦,你說他那個木牌啊,仵作司,左冷蟬那丫頭,看他可憐給他做的,上面刻的是捕頭。”王德說完看了眼前方,“你分不清材質?”
“我壓根就沒看到……算了。”洛陽懶得扯淡了,“所以他能打嗎?”
“能。”王德用力的點頭,“二境修為,全力打他一拳,都不帶掉很汗毛的。”
“那很厲害啊。”洛陽想到了常平那股子蠻力,下意識地夸了一句。
“是啊,能打。”王德從腳下扯了跟草,放進了嘴里,“能打。”
等等。
洛陽聽出了他話里的意思,有些不確定地推了推王德,“你說的能打,是哪個能打?”
“你覺得呢?”王德反問道。
沉默片刻,洛陽試探著問道,“那他能打別人嗎?”
“他不會打架。”王德的聲音有些苦澀。
“那我找個沙包回來干嘛?”洛陽睜大眼問道,“感情他除了力氣大些,就光會挨打了。”
能打,原來是這個能打?
“我咋知道?”王德小聲嘀咕道,“又不是我找的。”
“我……”臟話終究沒能說出口。
“要不我們回去想想辦法再來?”王德問道。
“可能來不及了。”洛陽搖頭。
“那大人可找到證據,證明這事是張二爺做的了?”同樣的問題,只是這一次問問題的人換成了王德。
雖然是在問洛陽的意見,但是王德不覺得眼前這名年輕的上司能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就搜集到足夠的證據。
畢竟能找常大做幫手的人,還能指望他什么。
果然。
“沒有。”
洛陽覺得自己確實不適合做捕頭,至少被自己抓住的那兩個人不該就那么掛在樹上,不聞不問。
想來現在已經跑遠了。
若是換了一名有經驗的捕頭,先帶回衙門再說。
“那我們沒辦法這么進去揉人。”王捕快說的很認真,“我們是衙門衙門辦案那是要講究證據的,別說洛陽只是一名捕頭,哪怕是趙巡,甚至是廖生在這里,也不能無端將人闖進去搜人。
這里是大唐,那么就得遵循大唐律法。
王德知道洛陽很年輕,也知道他對衙門里的事不太了解。
可作為捕頭,這種最基礎的常識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當上捕快的,又是怎么升職為捕頭的。
難道真是上面放下來鍍金的?
“那怎么辦?”
“闖進去,搜人。”洛陽平靜地說道。
“你是認真的?”王德瞪大了眼問道。
洛陽看了一眼王德,心說我沒事和你開玩笑?
“就我們兩?”王德難以置信地問道。
“也可以是我一個人。”洛陽覺得這事自己得負責,那么出事了也該自己背鍋。
“闖進去,可能比搜集證據更難,那可是張二爺,在西湖邊上叱咤風云的龜張,光他手下的人,就我們兩,憑什么打得過。”忽略了年輕人逞強的話語,王德自然不會看著洛陽一個人就這么沖進去。
鬼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著自己。
“蔡寧就在里面。”洛陽的語氣很堅定。
“可我們這么闖進去,他們對蔡寧下殺手呢?”王德試圖糾正洛陽這種偏激的想法。
“如果我們再不把人救出來,那么就不用救了。”洛陽從地上站了起來,看向那兩盞高高掛著的燈籠。
張二爺已經派人對蔡寧的母親出手,雖然恰好被自己攔住了,可這正說明蔡寧現在的處境并不妙。
不管張二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選擇對蔡寧出手。
他這樣的行為,是在挑戰大唐律法,被抓到搞不好是要掉腦袋的事。
洛陽不相信他會再把蔡寧放出來,也許那個油嘴滑舌的年輕捕快現在已經是一具尸體了。
王捕頭應該也想到了,只是他沒說出來。
畢竟是做了幾十年捕快的人,這點眼力勁還是有的。
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趨勢張二爺選擇了這樣一條路?
就因為一頓毒打?
不可能。
王德第一時間作出了判斷。
洛陽或許知道,可看樣子他不愿意說。
難道真的只能像洛陽所說的,闖進去,搜人?
不說張二爺豢養的打手,這可是強闖民宅,回頭職位丟了不說,搞不好也得進去蹲兩年。
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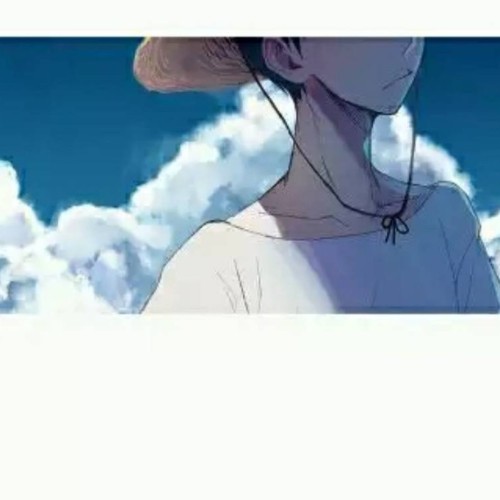
問劍青城
惆悵,怎么就被盯上了,沒感覺沒違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