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2005年海南島歡樂節,美國的華文媒體《世界日報》記者應邀來訪,我負責聯系。他們離開前向我約了一篇專訪稿。
當年11月23日,《世界日報》刊發了我作為特約記者的署名文章“海南島是一個新聞富礦”。
薇在華盛頓她小姨小何老師的書房里看到這篇約稿,也看到了按她的說法是重名率很低的我的名字,認定這個人就是我。
她通過世界日報聯系上了我,并在看到文章后第三天來到了海南。我們在三亞亞龍灣住了6天,回憶往事,重溫舊夢。
我倆躺在床上說著話,薇突然讓我轉過身,她用手指輕輕推了推我背上的黑痣,好像想驗證它的真假。
“記得有一天,你看到我背上的黑痣,你開玩笑說我們背上都有一粒痣,卻在各自脊椎的左右兩側,是一種不祥的預兆。”她說,“當年沒把它當一回事,現在看來這一切也許真是命中注定!”
薇說,出事的那一天,她在家里躺了一整天,特別想見我,想與我談談出國的事。
晚飯后,她到我們學校找我。她知道我們去曉港公園燒烤,但估計我已經回來了,所以直接上了我們宿舍,結果沒見著我,就在我們宿舍樓下等。后來想上洗手間,她去了她小姨的宿舍,看到了令她撕心裂肺的那一幕。
薇說,沒曾想過她這一輩子會遭遇那樣的傷害。一個是她最親近最信任的親人,一個是讓她總是懷揣甜蜜、憧憬美好,情竇初開就想托付終身的心上人。這兩個人就這樣聯手在她面前將她的初戀糟蹋得面目全非,慘不忍睹,將她的精神家園蹂躪得粉碎,是那樣地直接、徹底,而又具體、真實,無容回避,不給自己留有一點回旋、幻想的空間。
她說,她在國內的那十多天,整個人空乏虛脫得好像靈魂出了竅,常常在噩夢中哭醒。
薇說,到美國后,她媽媽帶著她去看了近三個月的心理醫生。在這期間,當聽說她小姨小何老師也要過去,她很抵觸,極力反對。最后小何老師不得不選擇到美國南方讀研,遠離薇生活的城市。
就在我畢業的第二年,薇考上了哈佛。她說,那一年她才逐漸從過去的陰影中解脫出來。
我對薇說,這些年來,每次談女朋友總是拿她作比照,再也找不到和她在一起的那種深深吸引、心心相印,再也找不到那種愿以整個生命來呵護和疼愛的感覺。
她說,后來她也慢慢理解,其實因為這件事受到傷害的不止是她自己一個人,她也就不再記恨什么了。
離開亞龍灣的前一天晚上,她默默地收拾著行李,從箱子里拿出一個執信中學的信封遞給坐在床沿邊上的我。
泛黃的白色信封里面裝著兩樣東西:一個是我曾經用過且最喜歡的瑪瑙匹克,上面刻著葫蘆形狀的我的名字。我在這個匹克的尖端打了個洞,穿過紅線,做成項鏈,在她十五歲生日的那一天親手戴在她的脖子上。一張是我們在海印大橋上的合影,這是我與薇唯一的一張合影。她哽咽著說:“我再也不想帶著它們啦”。
薇說,出事那一天回到家,當她小姨來到她臥室,看到她小姨,她就拼命地想扯斷我給她戴上的這個匹克,直至脖子被勒出一道道血印。她小姨在身邊看著心痛,急忙找來剪刀剪斷了它。
薇隨后將它拋出了窗外。臨去美國收拾東西時,薇發現它就架在窗臺上,腦袋上耷拉著剪斷的紅線子,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這讓她睹物思人,觸景生情,熱淚盈眶。最終她還是扯掉線子,把它放進了行李箱的夾層。
看著手里的東西,聽薇說著,我突然失控,捂住臉嚎啕大哭。
她走過來,母親般把我攬入懷中,讓我的頭靠在她的胸前,任由我哭泣,直到我平靜下來。
我說:“把它燒了吧”她不同意,說不吉利。她若有所思,說:“要不明天早上去游泳時把它沉下海底,讓它永遠留在這個我倆都喜歡的地方?”“好吧!”我故作欣然接受。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我們換上泳裝去往沙灘,薇帶著那個裝著匹克和相片的信封。
下水時,我單手舉著它,一直向前游去,薇跟在我的后面。我們游過防鯊網,一直向前,直到她再三阻止我。
我們踩著水,面對面手牽著手把信封放在我們之間的水面上,看著海水慢慢把它浸透,呈“之”字形輕盈地敲打著我們的身體往下沉。我倆不約而同地潛入水中看著它,直到從視線中消失...
八
我啟動了發動機,沿著跑了無數次的路線行駛,車竟然又轉回了機場停車場,我才不斷提醒自己集中注意力,留心路邊的指示牌,沿著指向,向HK市區方向使去,重新進入我生活的正常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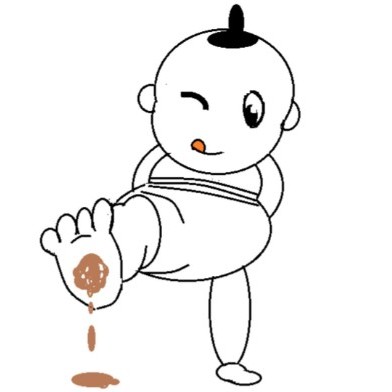
吳楚魏
故事結束,感謝閱讀
